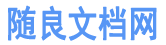岁月积累的疼爱
我没去过台湾,我想跟你说说我婆婆去台湾的事,但是你可能不想听。那好,我们就直接说潘越云吧。
潘越云是个台湾歌手,好像一直待在台湾,连香港歌坛都很少涉足。算起来,她唱了有30年了。我也断断续续,跟着听了20多年。
她的声线是属于游移不定的那种,游移到她自己控制音准都有点困难。一般我会认为,这种声音有诗歌的特质,是才华的显现。这样的声音,唱戏人家肯定是不要的,唱美声也会被嘲笑。它不属于被规范的范畴,有点危险,只能任其自由地发展。流行歌手中不乏这样的声音,诸如比约克,山羊皮,黄家驹。
有了这种声音,很难说幸或不幸,尤其是在潘越云的年代(现在是这种声音受宠的时代)。因为那个时代的歌曲,显然还是有点保守的,民歌的痕迹很重,配器也简单。那是个属于龙飘飘、凤飞飞、邓丽君、刘文正的年代。吐字发声和音调的掌握都要圆润丰满并且祥和对称。潘越云的歌声是不圆润的,如裂帛,撕开丝绸的感觉,并且从不走直线,总是倾斜而出,不指向你预测的位置,突然爆发上去,又很快滑下来,滑到很低,低到深不可测。听她唱歌,是一种危险的体验。被邓丽君训练出来的耳朵不是很好适应,如同坐木马和坐过山车的区别。但是她却让李泰祥、李宗盛这些才子们兴奋。那时期有两个人集中诠释了他们的作品,将台湾流行音乐带到了一个清丽脱俗的新方向。这就是潘越云和齐豫。齐豫像一只鸟,飞到了云霄,潘越云则如鱼儿,游到了深海。她们带我们去的地方,都不是常见的风景。邓丽君们,始终在人间。人间自然也好,如同心灵鸡汤和现实主义小说,但是,偶尔的夜里,面对遥远的星空,我们也需要诗篇。她们就是这样的诗篇,齐豫让我们忘记了俗世,潘越云像一根针,刺中了我们的心。这确实是声音的贡献。有时候,同样是一首人间的歌曲,别人唱得祥和,潘越云却会唱得更深刻。她就像一片乌云,漫过之处,就会下雨。很多人就是从听到她的那一刻起,爱上了苦。爱上这样的味道,如同爱上了一种缺点,品味就远离了大众。也如爱上榴莲的口味,上瘾。
很奇怪,即便如此,有点另类,我却一直觉得,她的歌最能代表台湾。齐豫有点洋化,蔡琴身上有现代知性的气息。邓丽君呢,身上的台湾特点也不是很鲜明,有点日化。潘越云唱过很多台语歌,像《天顶的月娘》《桂花巷》,很明显的台湾小调的曲式,就连歌名,都唯美精致,富有闽地特色,接近我臆想中的古典的台湾。我婆婆一直想去台湾的理由,就是因为那里有保存完好的传统文化,从人的礼仪、饮食到文化气息。对于一个做了一辈子医学工作,并热爱时装、烹饪和书法的老太太,这些很有吸引力。我也毫无明确理由地一直认为,台湾对中华文化的传承是连贯的、温和的。在潘越云的台语歌里,你可以听到一种隐藏不住的温柔,这是一个中国女人的意蕴。她还唱过很多台湾电视剧的主题歌,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经历。如同刘欢之于大陆,罗文之于香港,是一种歌声地理的标签。在唱这些歌曲时,潘越云将声音放淡,淡下来,声音就好控制一些,哀愁也就跟着淡了,离中国式审美也就近了。还有她的长相,我觉得也很台湾。突出的前额,高高的颧骨,典型的南人面貌。初看虽然有点突兀,却并不摄人,因为眼神和气质中的自信都是含蓄的内敛。
当然,这些印象的获得是岁月的积累。就像我婆婆想去台湾,惦记了不是一天两天。
有几位女歌手,包括蔡琴、齐豫、潘越云,一直被我这个年纪的女人在心里偷偷当阿姨般爱,爱了很多年。说阿姨,有亲情的意味,她们就像我们在远方的亲戚,小时候宠爱过我们,收留过我们的心事和眼泪。她们美丽,是我们青春期向往长大后成为的样子。她们将一直美丽,我们不允许别人说她们老,即便在生活中有了些许瑕疵,也不影响我们对她们歌声的忠诚。这么多年,我们早就相信了,她们是懂得深情的,而我们自然也是。我们不会像布兰妮的歌迷,朝三暮四。
有些感情是岁月的馈赠,属于当事人双方。别人是无法破解的,也无法原样拿走。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渐渐懂得,听歌有时候听的是这份感情。
潘越云的歌声是内向的,不伤别人,只伤自己。她因而更让人疼爱。
与神的两种极端关系
那些差强人意的嗓音,朴树、郑钧、许巍、崔健、张楚、罗大佑,甚至B.B.KING,鲍勃·迪伦,演唱着旋律优美至极的歌曲,你仿佛就看到了美人被摧残。听许巍常常会有这种感觉,那些配器实在太美了,美到他一张嘴有点失望。从前,我总是满怀遗憾地,边听边感慨造物主的吝啬。他们的声音和音乐站在一起,如一个布衣少年伴着一位美得令人震颤的仙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仙女与少年彼此相爱,不可分离。因为他们一旦离去,仙女就会丧失魔法,变成村姑。如此说来,他们是有魔力的。但他们从不伪装成神,他们就坚定地呈现人的朴素、缺憾、原生态,散发着人间草根的清香,令你觉得真实。摇滚的魅力正在于此。让你看到人的局限和坚强,好比西绪福斯。假如音乐真的是神,他们也是以人的身份在挑战神,企图平等。这是真正令我感动的。
加缪在《西绪福斯神话》中讲,西绪福斯与神对抗,受到惩罚。上帝命他终生重复一件徒劳无益的工作,每天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再看着它滚落到山脚下,周而复始,没有尽头。上帝以此对人类进行了嘲弄。加缪从这个神话中发现了人生的秘密,他认为人生做什么都是徒劳无益的,在神面前,人类是卑微的。这是一个前提,但不是秘密的全部。秘密的后一部分是个哲学问题,也是个宗教问题。即人类如何面对这种命运?叔本华认为,人生如钟摆,在无聊和痛苦之间摇摆。只有追求内在的精神可以摆脱这种无聊和痛苦。佛教要求人修此刻而求来生,基督教告诉你有天堂。幸福基本都在死了以后,没今生什么事。法国皇帝路易十五很生气,说:“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生活中因而比比皆是及时行乐的人。加缪还有别的道路吗?没有,他不探讨道路的问题,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结局已经被神规定了。必须面对,正视命运和现实,进而去享受和欣赏这种荒诞。他说,西绪福斯只要不停止工作,就没有向神妥协,就一直在对抗。只要他坚持住了,就呈现了人类绵绵不绝的力量,就没有被神看到笑话,反而以此嘲弄了神的权威。人类,唯有此一种方式,可以在卑微中显出伟大和高贵。加缪比谁都真实、坚强,如一位站在暴风雨里赞美痛苦的歌者。
摇滚的精髓就在于人本和真实,不虚伪,不媚神。声音的不装饰,也是人本和真实的一部分。
新世纪音乐(NEW AGE)刚好相反,它追求极致的和谐之美,人在才华的驱使下接近着神。恩雅(Enya)的音乐当中,声音可以视作一件乐器。她的很多作品,没有歌词,人声只在哼鸣。这姿态是归属式的,对神的皈依。将自身视作自然的一部分。新世纪音乐中,人声与乐音绝没有冲突和对立,甚至在技术上的对比都没有。他们要做的,就是脱离尘世,抵达神界。表达者需要的才华,是空灵式的。让人烟从乐曲当中消失。
但,我们终究是人,不是神。人,试着去做神的事情,总会有痛苦。这种痛苦是隐蔽的,它不同于摇滚歌手,摇滚歌手将缺憾摆出来,他们就是要和神对着干,他们报复似的做人。对空灵的追求到达极致,人会厌倦自己。心灵会站在遥远处蔑视肉身。肉身的速度,就是奥运会纪录的速度,是有极限的。而人的心灵,与神相通,无极。
于是,有了阉伶歌手,这种以戕害身体抵达完美的道路。资料记载,阉伶歌手最早出现在16世纪,当时因为女人不被允许登台演唱,人们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声音条件好的男童在其进入变声期以前,阉割。阉割掉的男童发育后具备了女人的音色,而其肺活量却还是男人的。他们的音域因而神奇般地,超过了常人的三倍。当然这是始料未及的结果,却造就了歌剧美声的辉煌。17、18世纪阉伶歌手的盛行,大大发展了各种歌唱技巧,因之在声乐史上被称为“美声歌唱的黄金时期”。有一部意大利电影《法里内利》(Farinelli Castrato),中文译作《绝代妖姬》,讲的就是阉伶歌手法里内利的生平故事。如今,那些常人无法企及的美妙高音只能被深深缅怀。18世纪英国著名的音乐史学家查尔斯·帕尼曾这样描述1734年法里内利在伦敦演唱时的情景:“他把前面的曲调处理得非常精细,乐音一点一点地逐渐增强,慢慢升到高音,尔后以同样方式缓缓减弱,下滑至低音,令人惊奇不已。歌声一停,立时掌声四起,持续五分钟之久。掌声平息后,他继续唱下去,唱得非常轻快,悦耳动听。其节奏之轻快,使那时的小提琴很难跟上。”就连对阉伶一向持有偏见的伏尔泰也承认:“他们(指阉伶)的歌喉之美妙,比女性更胜一筹。”这是个极端的例子。空灵的艺术,通常都有无根之美。因为,艺术家太想脱离肉身,成为神。
这两条道路,摇滚和新世纪,我觉得前者的精神品质更高贵,而后者更接近艺术的极致。它们终将在一个人的理想中对峙。没有人会得到两全其美,因为没有分身术。假如互相嘲笑的话,也只是以自己的手嘲笑对方的脚。
听歌的人最无情
如果还一直记得《把悲伤留给自己》,离陈升已经太远了。那种唱歌的模式和美感早被他打破。我起初也是不能接受,怪他为什么不好好唱歌了?
他开始发出一些粗鲁的音调,像赤足裸背坐在街边排挡喝酒的男人。不和谐的滑音宛如低空划过地面的飞机,瞬间又呼啸着冲到天上去,将人群弃置身后。大概是从《SUMMER夏》那张专辑开始,我意识到了他内心的冲突。这是一种破坏的欲望,或者用“作践”这个词更合适。作践别人,也作践自己。用这个词,体现了一种态度,别人的态度,似乎他有什么痛苦,需要发泄。趋于不正常。那正是我当时的态度,隐隐含着失望。他明明可以一直抒情、优雅,散溢出些许忧伤,符合大众的审美。他身上具备了一切吸引人的唯美素质,为什么不珍惜?
亲手设置一种完美(他完全有这种才华),再肆无忌惮地用不和谐的形式打破,使深情残留其中,令人产生一种欲说还休的怅惘,如被捆缚住的感动,不能痛快。陈升出道二十年,在我看来,一直在做着这件事。他后来的歌曲始终包含着矛盾的两个方面,甚至多个方面,它们互相对比着衬托,也互相抑制着抵消。后来,我渐渐意识到,他可能并不是因痛苦才如此,而是,惟其如此,才让他舒展。这是一个蜕变的过程,由男孩成为男人。也是一个发现内心的过程,由单一地呈现到复杂地表达。从他自己的角度看,这种破坏其实如天马行空,有去除枷锁打破审美平衡的畅快,畅快淋漓,自由自在。因为,长时间维护单一,有时候是刻板地墨守成规。
陈升确是个不羁的男人。接受记者访问,他就穿着睡袍和拖鞋来,不是不尊重对方,他会认真地跟人家解释,台北的夏天很热,这样很舒服。开新歌发布会,他骑着自行车到现场,头戴花纹礼帽,T恤上还印着酷似他本人的卡通造型。一副很可笑的样子,却快乐无比。给梁静茹演唱会做嘉宾,他也着拖鞋上台,却又穿着LV的衬衫。他就是这样,以内心的真诚搭配外在的滑稽,似乎唯有如此,才接近他的真实。有点无厘头,像他一首歌的名字——《老嬉皮》。
关于他和刘若英,一直是大家喜欢谈论的话题。刘若英的演艺之路深受他的影响,走人文路线,他也对刘若英悉心培养,不遗余力,可以说是父女般的师生关系。另一方面,刘若英爱他挚深,至今未嫁,他却始终保护着自己的家庭,欲拒还迎。他是有些残酷的,不能交付全部的自己,便不能完整地接受对方。他只能交付老师的情感,至于情人的那一部分,始终有所保留。这些,真的是无奈之举吗?我不认为是。以陈升的性格,与其说他更有责任感,不如说他更爱自由,不愿受到感情的羁绊。家庭其实从来羁绊不了他,却给了他温暖和安全,惟其如此,他才可以更加放心地自由飞翔。而爱情是负累。他不是没有感情,相反,陈升的情歌感人至深。但他不愿意成为一颗痴情的种子,那样世界会变得过于狭小。他只是偶尔意识到自己的这一面,调侃自己是《多情兄》。这些矛盾住在陈升的身体里不肯睡去。别人会因此而痛苦,陈升则接受这些并学会了享受。他在《恨情歌》中唱:“于是我叫我自己恨情歌,假装我不在乎。或者我不再去讨你欢心,我喜欢这样的自己。”爱自由的人都是自我的,没有什么可以束缚他,他甚至可以“勇敢地拒绝全世界的要求”。拒绝,对很多人来说是件难办的事,陈升却能够狠下心肠。
在对待刘若英这个问题上,很多人倾向认为陈升很无情。但是没有他的残酷和严厉,也就没有刘若英的今天。当年刘的第一首歌《为爱痴狂》,陈升为她一录三四年,耗掉了至少三百万台币,直到满意为止。结果刘若英一鸣惊人。后来参演《少女小渔》,也是陈升大力向张艾嘉举荐的结果。对待艺术,陈升是个近乎苛刻的人,对待极为喜爱的刘若英就更加苛刻。这种爱的表达方式,是陈升式的,正如他的歌曲,暗涌的深情,又被他用粗糙的唱腔刻意消解掉。他永远都站在矛盾的中间,以虐待来享受,以无情表达有情。此等高贵的深情,岂是那些无情的人能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