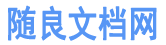18世纪中叶,德国哲学家鲍姆嘉通在《美学》(第一卷)中第一次将美学与逻辑学、伦理学区分开来,在严明规定逻辑学、伦理学的定义和研究对象之时,也通过“感性学”规定了美学的研究对象并赋予美学救赎人生的功能。故此,标志着学科形态的“美学”诞生。康德在鲍姆嘉通美学观点上又通过一系列的判断力活动论证了人类主体自由的本质力量,使美学的学理依据真正确立起来,成为彰显人的主体性的学科体系。
20世纪初叶,王国维、蔡元培通过翻译外文、撰写文章等方式将美学引入中国的文学艺术界。此后,无论是在近代还是在现当代,受社会形态、社会主流话语等不同因素的影响,美学都会间隔一段时间“发热”,并不断建构、完善着中国美学的学理框架。
整个20世纪,中国美学在30年代、50年代、80年代先后出现三次大规模的“发热”现象,从学习西方美学到为国家意识形态服务,再到文化精神的自我甦生,中国传统美学在与西方美学、国家文化形态的融合中循次而进,建构了不同时代话语下的美学体系,并影响着与其关系密切的艺术学,对各艺术门类的创作、表演、研究均产生了影响。舞蹈艺术虽在整个艺术发展史中受到美学的关注较晚,黑格尔等人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尚未承认舞蹈美学的存在,但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通过“西学东渐”将美学引入国内之时,中国的舞蹈艺术便随即受之感导,在美学思潮影响下形成了显明奇特的舞蹈景观。
一、“美学热”中的“为人生而舞”
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学热”中,王国维始作俑者起到了开创作用。他学习了西方康德、叔本华等人的美学思想,并在翻译外文著作时使用了“审美”“美感”等现代美学词汇。此后,他又开始尝试将西方美学理论和中国乾嘉学派的传统美学结合起来,论证艺术对人的救赎作用。他认为:“美术(艺术)既与人没有利害关系,又能使人忘却自我、超然于现实利害关系之外,担负起解脱人生痛苦的作用。”[1] 继王国维之后,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推波助澜,在北大开设了美学课程,指出美是自由的、进步的,宗教是保守的、强制的等关于“以美育代宗教说”的观点,多次发表“足以破人之我见,去利害得失之计较”的审美主张,此观点在当时得到广泛传播,并成为20世纪30年代美学热的主题。此外,其他参与此次美学热潮的翘楚们:胡适、鲁迅、范寿康、吕荧、邓以蟄、朱光潜等人也都围绕这个主题撰写了大量文章或出版书籍。如吕荧在西方“移情说”的基础上编写的《美学概论》、朱光潜在“直觉主义美学”基础上编写的《文艺心理学》等,其主旨思想均与“审美无功利”的美学观点相契合。可见,20世纪中国美学的第一次发热,是西学东渐带来的一次学术探讨,美学家们大量引入西方的美学观念,再结合中国传统美学,大力宣扬艺术的审美救赎功能,为20世纪初各门类艺术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在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20世纪初叶,舞蹈艺术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发展态势:一是许多知识分子为了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倡导在体育课中增加舞蹈内容,实现强健体魄的目的。并且受蔡元培“美育”观念的影响,许多小学开设了乐歌课、舞蹈课,以黎锦晖为代表创作的“学堂歌舞”成为这一时期中国舞蹈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欧美交际舞在旧上海的风行。在商业文化扭曲发展的情况下,这种交际舞很快就沦为可被出卖的商品,与“美学热”倡导的审美救赎功能、艺术非功利性等观点几乎完全背道而驰,冲击了中国传统舞蹈的观念和形式。期间,中国的新舞蹈艺术虽然也曾在报纸、演出中显露端倪,如上海的《申报》《大公报》上刊载的有关传统舞蹈研究的文章、吴晓邦三次赴日本留学期间在上海举办的“个人作品发表会”,但由于受到种种限制这些舞蹈活动传递的观念尚未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影响。直到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国的新舞蹈艺术才冲破了桎梏,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成为培养人高尚情操、帮助人树立正确价值观的艺术。
1937年吴晓邦高举“为人生而舞”的大旗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等作品,标志着“新舞蹈艺术”开始向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势力的宣战。之后他又演出了《傀儡》《小丑》《拜金主义者》《丑表功》等前期创作的作品、新创作了《罂粟花》《饥火》《思凡》《宝塔与牌坊》等作品,有力地控诉、讽刺了旧社会的黑暗和敌人的残暴,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进步作用。以《宝塔与牌坊》为例,这部作品将中国封建伦理道德中最典型的标志“宝塔”“牌坊”作为象征加以讨伐、控诉,隐喻出中国封建社会不民主、不自由、不尊重人权的现实。通过创演艺术作品的方式帮助人们认清实际,宣扬人性的自由解放,鼓舞人们斗志的还有留英归国的舞蹈家戴爱莲,她在30-40年代的美学热潮下创作了《警醒》《前进》《东江》《思想曲》《合力》等作品,这些作品不仅以真挚细腻的情感、意蕴深邃的内容、新颖独特的形式为新舞蹈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唤醒了更多民众从封建专制主义中走出来,奋起投入到抗日的斗争中。
20世纪30年代的“美学热”在影响舞台舞蹈创作之时,民间舞蹈通过党的文艺方针也悄然发生转变。在追求人性自由解放的美学主题下,民间舞蹈摆脱了原有的封建迷信印记,以陕北地区“鲁艺”秧歌队为代表的民间歌舞队伍对传统民间舞蹈的不断改进和创新,使民间舞蹈迈出了改革旧歌舞形式的第一步。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便是20世纪40年代遍及整个解放区的“新秧歌运动”,它使民间舞蹈从内容到形式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在作品内容上,密切结合现实,反应人们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一扫旧秧歌中不健康的内容;其次是队形变化上,在传统阵势的基础上加入了新的程式,赋予作品新的含义;最后在动作形态上,演员手、脚部位的动作都摆脱封建社会原有的审美特性,注入了鲜活的时代基因。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学热”的余温尚未散尽的40年代,延安新秧歌运动中诞生的《兄妹开荒》《胜利腰鼓》等作品影响了戴爱莲、彭松等人的舞蹈创作,在经过对少数民族民间舞蹈的采风、加工、整理后,1946年举办的“边疆舞蹈大会”首次公演了瑶、羌、彝、藏等少数民族舞蹈,探索出了中国民间舞蹈创作的新路径,也为新中国舞蹈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总体来说,20世纪初文人志士的民族自觉开始迈出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步伐,中国文学艺术界在西学东渐中借鉴了西方美学并结合中国传统美学,引发了持续已久的美学热潮,在“人性解放”“审美无功利”“审美救赎”等美学思想的观照下,学堂歌舞、舞台舞蹈、民间舞蹈的创作观念都发生了积极的转变。舞蹈家为人生而舞的艺术观念,舞蹈作品积极进步的内容和鲜明别样的新形式都与美学热潮中热议的主题形成关联,中国的舞蹈艺术也在美学思潮影响下开始从纯娱乐和唯美主义中解放出来,积极地反映现实生活,成为培养人高尚情操、树立正确人生观、为人生而舞的艺术,形成了20世纪第一次“美学热”下“为人生而舞”的舞蹈景观。
二、“美学热”中舞蹈艺术的政治化倾向
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是在党的“双百方针”影响下围绕“美的本质”展开的一次探讨,虽依托50年代政治大环境,不言自明地带有政治语境,但讨论中对峙的美学观点和讨论的结果却深刻影响了20世纪50-60年代的文艺创作,使文艺创作者站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视角,创作出一批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社会主义文艺作品。
在这次美学讨论中,美学家朱光潜成为首要的攻击对象,由于旁征博引地借鉴了西方的“移情说”“距离说”等主观说观点,他的美学理论被视为“资产阶级思想产物”,覆盆之冤使他率先进行了自我美学批判,站在马列思想的角度申明自己“主客观统一”的美学理论。不过,黄药眠、蔡仪等人在《文艺报》上仍猛烈抨击了朱光潜的美学思想,并由此引出“美在客观说”的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紧随其后,以吕荧、高尔泰为代表主观派却又在反对“美在客观说”的基础上提出“美是人的一种主观观念”。在这几派美学家持各自观点围绕着“美是什么”展开了激烈论战时,后起之秀李泽厚在“马列主义美学思想”的指引下,振聋发聩地指出“美是具体形象性和客观社会性统一”的观点,把美看成是物的社会属性,认为自然本身不是美,美是自然社会化的结果,也就是人的本质对象化的结果,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显然,李泽厚美学观点在对“美的本质”阐述上融合了客观实在性、社会历史性,相比此时期其他美学观点关于“美的本质”阐述更为全面,更具有说服力,也因此成为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影响较大、较为深远的美学观点。
新中國成立之初的50年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中国在文艺创作上接受了苏联的指导,主张文艺的党性原则,认为文艺应当是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要为工农兵创作,为工农兵服务。因此,李泽厚在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发表的观点无疑也受到文艺政策的影响,他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的观点为支撑,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政治背景,给出了更符合政治观念形态和历史形态的美学观点,体现了社会主义初期国家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指引和思想改造。
在这次的美学大讨论中,舞蹈艺术虽未形成完备的美学体系,但是美学大讨论的观点却渗透在舞蹈艺术的创作中,引导了舞蹈创作的走向。在群众舞蹈方面,1958年《新文化报》和《舞蹈》相继发表《积极开展全民舞蹈运动》的社论,1960年在京举办了全国职工文艺汇演,推出《巧姑娘》《英雄矿工》等群众舞蹈节目,在之后的5年里,天津、北京、贵州等地又举办了十余场职工业余舞蹈专场的汇演,演出了《葡萄丰收》《丰收乐》等舞蹈作品。在舞台民间舞蹈的创作上,编导从现实生活出发,提炼各少数民族富有特性的动作加工创作,推出《快乐的啰嗦》《葡萄架下》《摘葡萄》《盅碗舞》《长鼓舞》等少数民族舞蹈作品,并在作品中流露出各族人民对社会主义中国的炽热情感和美好愿景。在舞剧艺术的创作中,以《小刀会》《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为代表的作品,将革命浪漫主义情怀融合在革命现实主义的题材中,热情讴歌了革命的胜利,纵情批判了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尤其是把关注点聚焦于工农兵、平民百姓身上的《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在芭蕾技巧中巧妙地运用了中国古典舞和生活的语汇,使芭蕾这门外来艺术成为中国人民在其自身文化建设中所获的艺术感悟与文化阐释,中国人民的声音、形象得到强有力的传递。从以上作品可以看出,在上世纪50年代的美学热潮中,现实主义题材的艺术创作被提上日程,舞蹈创作体现出对社会现实、革命历史以及人民群众的关注,这与美学热潮中李泽厚的“美的社会性”思想所见略同,与党在此时期的一系列文艺政策如“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应该采取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以及“音乐舞蹈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紧密相连,形成了美学热潮中鲜明的舞蹈景观。
除了舞蹈作品的内容呈现出显著特征,并由此形成美学热潮中的舞蹈景观外,这一时期舞蹈作品的体量也在建国以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1955年《舞蹈通讯》的第一期,便开展了“舞蹈创作为什么贫乏”的讨论,随后1958年开始的生产“大跃进”也影响了文学艺术领域的“大跃进”。尤其是1959年全国文联提出“鼓干劲,争取文艺更大丰收”的号召后,各民族、各省市纷纷展开舞蹈会演,仅1959年就举办了20余场有关舞蹈的展演,大型舞剧多达9部,小型舞蹈作品的数量更是不计其数,但由于这一时期政治的干预,部分作品成了政治宣传的工具,限制了艺术的自由创作,其作品质量并未能与数量的剧增形成正比。显然,作品“体量之大”与这一时期的“大跃进”“大字报”“大鸣大放”等一样,带有鲜明的鼓吹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语境,就连“美学大讨论”也难免是一次披着“学术”外衣的政治运动。因此,在声势浩大的舞蹈景观中,舞蹈作品的体量之大与作品内容的现实性、社会性同样是受到了政治性干预。
上世纪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虽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但为中国当代美学的构建起到了铸型作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传播。舞蹈艺术也受“美的社会性”等美学大讨论中核心观点的影响,与文艺政策密切相连,形成了在美学大讨论下政治性鲜明的舞蹈景观。
三、“美学热”中彰显人性自由的舞蹈艺术
20世纪60年代中叶,政治领域的“文化大革命”使国内文艺的发展也被卷入到革命大潮中,文艺创作进入了“文革”的畸形发展期,艺术的外部形态和意识形态都受到了桎梏。但在十年文革结束后,被束缚的思想意识在新时期有了广域的言论空间,1978年《诗刊》率先刊载了毛泽东在60年代写下的一篇关于“诗歌形象思维”的文章,随后朱光潜、蔡仪、宗白华、李泽厚等一批有影响力的美学家纷纷加入到“形象思维”的讨论中,翻译外国的原著并撰写相关论文,就此拉开了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
在这次美学讨论中,朱光潜率先扛起了大旗,他从马克思的《手稿》中寻找思想资源,发表了《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和共同美的问题》一文,把人性归结为人的自然本性,呼吁文艺创作要冲破人性、人道主义的禁区。随后,朱光潜因不赞同他人的观点,又从美学角度重新节译了《手稿》,以郑涌、张志扬为代表的美学家为支撑自己的观点也纷纷节译《手稿》,就此引发了80年代美学界持续多年的《手稿》研究热潮。从今天来看,在将《手稿》转换为自己研究思想的过程中,李泽厚无疑是最成功的。他在《美学的对象和范围》一文中指出:“美的本质和人的本质是一致的”“人性是感性与理性、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等关于“人性”本质的解读。对比朱光潜和李泽厚的观点可以发现:朱光潜阐述的“人性”“人道主义”是抽象的、形而上的人,并没有落实到作为个体的人的自由、解放以及困扰个体的精神深层的问题。而李泽厚的“人性”是建立在“实践美学”上的具体人物和具体情节,是将空洞抽象的理论具体到了个体,是普遍与特殊的统一。但不论是抽象的人性还是具体的人性,在这场“美学热”中都是将“人的感性生命解放”作为了美学主题。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岳川教授认为:“美学热是被压抑的感性生命解放的勃发形式,当思想解放以美学热的方式表征出来时,美学实际上成为当代新生命意识存在的浪漫诗意化表达——对人自身感性存在意义的空前珍视和浪漫化想象。”[2] 显然,80年代的“美学热”已不再纠结于文革时期政治语境,也不再是“主客二分”的两极争论,而是美学界的一次意义伸展的学术探讨、一次思想解放的美学自我甦生。
美学界的再度“发热”,也促发了舞蹈界文化意识的觉醒与创作的激情。1978年中国舞蹈家协会在文革时期被迫禁闭后重新运转起来、《舞蹈》杂志恢复出版、北京舞蹈学校升格为北京舞蹈学院、1980年全国第一届舞蹈比赛的成功举办……这些文艺体制上的恢复与重建为美学热潮下舞蹈创作作了有益的铺垫。
在新时期下,《惊梦》等一批中国古典舞的经典作品重登舞台,中国古典舞在重温经典中开始寻求对古风的突破。以门文元的《金山战鼓》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舞在第一届全国舞蹈比赛中一展英姿,作品的英雄主义主题并没有陷入空洞的说教,而是将戏剧冲突与人性色彩相结合,在情节演进中塑造了情感细腻、性格突出的人物形象。更具有历史意义的是中国古典舞“身韵课”的问世,“身韵课”使中国古典舞超越了技术层面的追求,开始挖掘传统艺术的精髓与本质,寻找传统艺术的内核所在,最终确立了中国古典舞的审美属性和审美品味。在美学热潮的影响下,中国古典舞在找寻本质和人性的同时,民族民间舞的创作中心也发生了转移:从最初简单的反应及歌颂生活的模式转向了刻画人物心理与抒发人物情感。以《水》(编导刀美兰)和《雀之灵》(编导杨丽萍)两部傣族风格作品为例,这两部作品的编导都抓住了傣族舞蹈的动律内涵,摒弃了风格化动作的堆积,前者在提炼生活语汇的基础上,将照镜、梳妆、洗发、甩发等动作语汇的发展逻辑与情感逻辑相结合,设计出柔美温婉的体态,营造出清新自然的意境;后者用富有灵性的肢体诠释了孔雀的自然、自由,传递出了强烈的生命意识。此外,这一时期的《小溪、江河、大海》《奔腾》《黄河》等作品也连锁性地发生了创作中心的转变,从情感内容的挖掘、动作语言的变通、文化内涵的凝练、舞蹈形象的重塑都鲜明表现出编导创作理念与美学热中“人性表现”的契合。
在中国古典舞、民间舞与美学一起提高热度之时,现代舞也在美学热的影响下关注着人的感性生命之解放。1980年华超在借鉴西方现代舞创作理念和运动方式基础上创作了《希望》,借助舞蹈本体申明了自己对“人性”本质的解读。《希望》没有采用任何的风格化动作,通过人物的心理外化直抒胸臆,使人们认识到:不用风格鲜明的民间舞动作、形式意味浓重的古典舞动作,仅用身体的颤动、呼吸的节律就可以表现人类深层的内心情感。此外,贾作光通过《海浪》同样展现出了新时期舞蹈创作的新理念,作品对蒙古族的手臂动作加以变异,在双重的艺术空间中塑造了海燕、海浪两个艺术形象。作为80年代受历史精神折射的两部作品,在创作理念和肢体形态上都展现出被压抑的感性生命的勃发和创作的自由。
小型舞蹈作品在争奇斗艳、凸显个性的之时,“美学热”的主题也通过创作理念、创作手法、动作语汇等多方面影响着大型舞剧的创作。新时期的第一部大型舞剧《丝路花雨》在重温历史中一炮打响,从敦煌壁画中提取素材加以创作,塑造了“S”型曲线造型,并以十几段独舞塑造了英娘的典型形象,仅从对艺术形象的关注来看,《丝路花雨》的创作就与“美学热”初期强调的“形象思维”形成一致性。此外,《家》《祝福》《雷雨》等舞劇作品逐渐开始从表现人物的内在心理出发,借鉴西方交响编舞法或意识流的手法,在形象塑造上摆脱了传统模式化、脸谱化的倾向。在舞蹈本质特征的探索上,舒巧通过《奔月》等作品探索出“结构语言性”的舞剧观;《无字碑》从“人性”着笔,以情感色调结构舞剧展现了武则天的心理历程;《阿诗玛》通过“诗化色块结构”展现了云南民间文化的瑰丽色彩……这些舞剧作品的艺术探索显然已经超越了以往传统的“苏联模式”,在美学热潮的影响下,编导家们的创作理念已呈现出多元化态势,形成了80年代美学热潮下异彩纷呈的舞剧景观。
与上世纪30年代、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不同,舞蹈艺术不仅创作出部分与美学主题契合的作品,最为关键的是,舞蹈学科在这次美学热潮中开始建构本学科的美学体系。王元麟在《美学》期刊上率先发声,发表了《论舞蹈与生活的美学反映关系》一文。文中从批评江青“用舞蹈动作直接如语言那样讲故事”的思想出发,引用传统美学的观点,证明了舞蹈动作是由特定民族的社会实践决定的一种风格和美。于平在王元麟的美学思想的基础上,引用西方美学的诸多观点,否定舞蹈是“纯然形式”的说法,确认舞蹈动作的外部形态和内部属性是统一的,并且对审美意识、审美主体、审美对象等舞蹈美学范畴阐明了自己的观点。除此之外,叶宁、徐尔充、隆荫培、朱立人等也发文参与了舞蹈美学的讨论,80年代末,冯双白、吕艺生、于平的“关于舞蹈美学三人谈”以及舞蹈界参与世界美学大会,更是对中国舞蹈美学体系建构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美学思潮的观照下,舞蹈艺术开始逐步摆脱文学性的束缚,对外部形态和内部属性以及二者的关系都有了较为深刻、较为科学的探索与认知。中国的舞蹈美学也从80年代的美学热潮开始建构并逐步完善。
可以看出,舞蹈艺术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潮中展现出了深刻的认知力和旺盛的创作力,在50—60年代的大体量创作的基础上,对舞蹈的本质属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艺术家的创作思维和创作理念与“美学热”的“形象”“本性”“人性”等关键词形成关联,创作出一批具有时代精神意义的作品,撰写了一批关于具有美学价值的文章,形成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下的舞蹈景观。
纵观20世纪的三次“美学热”,中国美学体系的建构经历了超脱宗教束缚的审美救赎——受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文化精神的自我甦生三个显著阶段,最终消解了主客两体的“二元对立”,归结为面向人性本体与个性自由的艺术哲学,其学理广度与深度也逐渐拓展,进而建立起中国文艺美学的知识谱系。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物质文明的日益丰富,在其之上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呈现出繁华景观,美学作为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门学科,更是以其强大的规训力量辐射了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甚至诞生了“新闻美学”“军事美学”“爱情美学”等新的美学范畴。在美学不断拓展自己的场域空间的过程中,似乎出现了矫枉过正——美学的急功近利与滥俗倾向,这也致使美学界至今尚未出现新一轮的美学热潮。作为美学研究领域的舞蹈艺术,似乎也受之感导:一方面,舞蹈美学的研究不断深入,吕艺生撰写《舞蹈美学》从对“原始舞蹈”的关注开始延伸至“剧场舞蹈”,结合中西方舞蹈史上的实例,从本质论、本体论、审美论三个层面论证了舞蹈是“意识的肢体表现”。除此之外,各专家学者也以不同的视角对舞蹈美学予以关注并撰文立著;另一方面,新时期中国舞蹈的创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体量,小型舞蹈作品、舞蹈诗、大型舞剧的创演数目走在世界前列。但缺憾的是,舞蹈创作的质与量之间尚未形成正比,作品的质量低下,称得上精品艺术的寥寥无几,与美学的急功近利与泛化倾向具有相似的特性。
但整體来说,整个20世纪的舞蹈艺术在三次“美学热”的影响下为后人留下许多值得学习的内容,包括舞蹈作品、舞蹈书籍、舞蹈活动等等,为新世纪舞蹈艺术的教育学习、作品创作、文艺表演、理论研究都提供了可鉴之处。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
注释
[1] 刘春阳:《社会学视野中的20世纪中国“美学热”》.[J].文艺研究,2014(6):18。
[2] 王岳川:《文艺方法论与本体论研究在中国》.[J].广东社会科学,2003(2):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