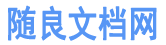体会与经验分享。正是这样有质量的小艺术节的存在,丰富了上海国际艺术节的面貌,也丰富了这座城市的文化面貌。作者在本文中以亲身经验分享了要做好艺术节的三个宝贵经验,以飨读者。
体会与经验分享。正是这样有质量的小艺术节的存在,丰富了上海国际艺术节的面貌,也丰富了这座城市的文化面貌。作者在本文中以亲身经验分享了要做好艺术节的三个宝贵经验,以飨读者。
“做大家都知道如何去做的事,只会使世界发生从1到n的改变,增添许多类似的东西。但是每次我们创造新事物的时候,会使世界发生从0到1的改变。”
——《从0到1——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美】彼得·蒂尔(Peter Thiel)
一
2006年初,在结束了长达5年的北京北兵马司剧场(简称“北剧场”)运营和退出北京大学生戏剧节的组织工作之后,仍在金融界奋战的我和几乎完全无业的戏剧制作人袁鸿,开始了一段晃晃悠悠的休闲时光。
人好像确实要空下来才有机会瞎想,开始说No之后才真正有机会选择到底要做什么。
停掉剧场,是因为明白,剧场只是百货公司,要往里面装东西。这东西得有人生产,不能光靠开百货公司的人。经营北剧场的那五年里,我们既要在没有任何政府支持的情况下独力支撑这个民营剧场,又要操心剧目的创作和生产,战线拉得很长,整个人的精力被消耗得非常厉害。
熬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终于决定放弃剧场,转战内容。很多年后,我在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给研究生上课时,一再跟他们强调:文化产业,内容是核心。一定要先做好内容,其他的才会随之而来。这些年电影业忽然兴起的IP疯抢潮,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这一论断的坐实。
退出大学生戏剧节的组织工作,一来是因为一些官方的资金和管理介入,削弱了当年我们初创这件事的“纯粹”之目的,有形的限制和无形的边界,使得剧目的创作和挑选,不再生鲜猛烈。且大学生剧社这种非职业戏剧的模式.无法形成有效的生产力累积,新人进来,才刚学会点儿东西,又走了。一茬一茬的接着换人,出来的东西永远在初级水平上,没办法实现真正的进步。
作为一个对于专业和完美程度有追求的人,我不想停留在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开始了新的寻找。
二
2006年至2010年期间,我们开始了专业戏剧的制作和大规模的巡演,光是和赖声川导演合作的明星版《暗恋桃花源》就在大陆、香港、澳门巡演了173场。加上其他的戏剧制作和巡演,那5年当中,我们充分累积了独立制作大型剧目和在不同城市、不同剧场之间辗转巡演的丰富经验,也进入了一个在外人看来相对顺风顺水的阶段。
可是,我自己的内心又陷入了另外一个瓶颈:长期的顺遂和安定之后,固定的运营模式和单一剧目,让这份工作变得不那么具有挑战性。尤其是国内的戏剧制作环境,越来越浮躁,明星的演出费高,票价也不得不水涨船高;若由没有知名度的演员担纲,票不好卖,而且这些演员因为有明星的案例在前,所以每个人心里都惦记着去跟影视剧,盼着早日出名,一有影视的活儿就走了。演出团队很不稳定,也没有平时的身体训练和长期培训可言,能到点儿进剧场就已经相当感恩了。
长此以往,整体的表演水平,其实一直在下降。我不是导演,有时候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也使不上劲儿。怎么才能让这些演员们受点刺激,愿意放弃一些名利的诱惑、好好留在舞台上练练功呢?怎么才能让观众在现有的明星戏和爆笑戏之外,看到点儿不一样的东西呢?
2010年3月,结束了长达三年多的“好日子”之后,我们又一次把自己放空。开始在祖国大地和境内外游荡,看戏,读书,用空白来释放心中积攒已久的疲惫和倦怠,等待新的方向出现。
那段时间,我们一直非常关注从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来中国演出的剧目,但平时主要是自己独立制作本土剧目,对于外来剧目,更多的只是看看而已,还没有想过可以自己主动地去引进。1999年,袁鸿在爱丁堡边缘艺术节看到了壁虎剧团的《外套》,剧团送了他一张完整的光盘,袁鸿带回来后没事就在办公室放给来访的朋友们看,有时候还带到大学和其他剧社去放给年轻人看。我跟着看了五六遍,每一遍都意犹未尽、感觉有新收获,惊叹于这些艺术家的创造力和舞台功力,那种能力,没有扎实沉静的创作和长年累月的舞台综合训练,是不可能完成的。
2010年,这个戏被国家大剧院邀请来演出,我们理所当然地帮忙做了些宣传工作,但因为和世界杯撞期,这个戏当时的演出效果不太理想,观众很少。我们当时就觉得非常可惜,后来又因有机缘合作,在同年11月把这个戏又请回来了一次,并在北京、西安、武汉、深圳四个城市进行了巡演,大获成功。成为在《三个黑故事》和《安魂曲》之后,最受中国观众欢迎的外国戏。
隔年8月,我在爱丁堡,又看到了大量小而精的作品,虽然不像《外套》那样气势恢宏,却也各有姿态、多元有趣。这个时候,我开始想象一种新的形态——怎样把这些中小型的戏剧作品,打包在一个品牌之下,让观众可以通过这个品牌而认知这些戏,同时又把这些戏的口碑,最终凝聚在品牌之上,形成持续的影响力,来不断宣介新的作品给观众。
2012年9月开始的“爱丁堡前沿剧展”,就是这样一个基于创新的实验,它最初的想法并没有那么清晰——只是觉得应该有一个“招牌”可以帮助大家识别这些戏,因为爱丁堡边缘艺术节是一个一年有30004000个戏上演的地方,鱼龙混杂、参差不齐,“来自爱丁堡”这个定语绝对不足以揭示我们所期待的定位,加上“前沿”二字才是我们真正的策展目标。
而我们也是第一个在华语世界里将Fringe翻译成“前沿”的,这一方面是因为“边缘艺术节”这一形态经历了从1946年至今60多年在全世界的发展,当年的“边缘”今天早已开始进入主流,并与主流表演艺术互动频仍、相互激励。另一方面是我们所选的剧目皆在水准之上,并非一般意义的实验与尝试之作,所以谓之以“前沿”,也藉此与国内戏剧一直被滥用的“实验”、“先锋”等水词划清界线。
2012年的“爱丁堡前沿剧展”,以西班牙默剧《安德鲁与多莉尼》开场,苏格兰国家剧院的音乐剧《屋中怪兽》、英国动作英雄组合的环境戏剧《看着我倒下》、香港邓树荣戏剧工作室的肢体喜剧《教室也疯狂》等紧随其后,加上一系列的放映、工作坊、展览等活动,剧展一炮打响,并且以巡展的方式走到了上海、北京、杭州、南京等多个城市,在当年的戏剧界赢得了强烈反响。
我们自己在后来的总结当中,意识到这个“创意”的成功,并非一朝所得。事实上它得益于我们当年在大学生戏剧节、在北剧场时做英国表演艺术节以及后来带着《暗恋桃花源》各地巡演的多重经验。有选戏的能力,有包装和官传的能力,有实际剧目运作的技术能力,这三种能力,成为剧展坚实的工作基础。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由于2012年至今我们一直致力于推动这个品牌的传播,现在每年8月的爱丁堡,都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戏剧人和观众出现,也开始有更多的主体愿意像我们一样在爱丁堡沙里淘金,寻找好的作品带回国内。
我们很高兴看到这一点,因为靠自己单打独斗,对一个环境的影响可能会有,却相当微弱。但如果有很多人开始做同一件事,这个平台就会越来越广阔。就像这几年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戏剧节和剧目,喜欢在他们的宣传词中也用到“前沿”这个词,这种精神力量的传递,会慢慢改变环境和书写历史。
三
在2013年短暂的修整之后,2014年的“爱丁堡前沿剧展”一下子扩张到了8个戏,巡演城市超过12个,全年演出112场,其中包括像《纸电影奥德赛》和壁虎剧团的《迷失》这种高难度的作品。我们对于剧目的选择,不仅开始影响到我国大陆的业界,也开始辐射到香港、台湾和东亚地区。像《安德鲁与多莉尼》经我的推荐成为台北国际艺术节邀请剧目,《纸电影奥德赛》在2014年9月首次到访中国大陆之后,于2015年3月成为香港艺术节的剧目,并在我们的帮助下于6月赴台湾高雄春天艺术节,同时二度来中国大陆巡演。
2015年,剧展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到12个作品。其中只有短短25分钟的创意物件剧《牧神午后》在北京蓬蒿剧场上演后,迅速成为城中热议的话题,在豆瓣网的评分飙到9.1分。苏格兰巴罗莱德舞团的舞蹈剧场作品《虎生》,是一部色、声、形、味俱全的4D体验演出,近景岛式剧场和演员的强烈互动,都为观众带来一种极为活泼的感受。而其中的精湛技巧与创意难度,也令大家赞叹不已。
在多年的策展工作中,我们始终坚持不能仅仅寻找那些只是在形式上新颖的作品,而是必须“秀外惠中”。这些作品必须同时兼顾形式与技巧双高标准,最好还立意高远、深刻动人。来自巴西阿默克剧团的《喀布尔安魂曲》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同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同行,以其过人的舞台功力,令我们刮目相看。
四
在运营这个自有品牌的同时,我们也开始了团队的转型。
这些年来,不断地有人找我们做剧场,因为我们有当年做北剧场的经验;也不断地有人想要投资或收购我们,因为我们的制作能力和组织演出的经验。我们都坚定地推掉了。
原因很简单,一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运营模式当中,我和袁鸿基本是义工,不拿工资,只报销一些基本工作费用。团队成员也很精干,常常一个人当三个人使。如果是由于自发和使命感,这种模式是可以运行的,但一旦被收购,劳动和智慧需要被正确估价,这个成本就会很高,我相信资方应该付不起。二是我不觉得我们目前这种形态有投资价值,说到底我们还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完全不以盈利为目的,很多时候一个戏能够做成,恰恰是因为我们不想着赚钱、只要不赔钱就行,所以它就做成了。如果一定要盈利,还要赚大钱,有很多我们想做的事,可能就没办法做了。
如果有人有钱给你,却反而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了。那要这钱来干嘛呢?
可是在这个不断被人试图“收买”的过程中,我也开始慢慢思考别人想要的是什么——那其实是某种“特殊能力”。如果我们不是整体地出售整个团队,而是出售我们的某种能力,会怎么样呢?
作为“爱丁堡前沿剧展”的策展人,我一直非常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那就是我们选戏和整体策展的能力。对于一个新的剧场或是艺术节展而言,通常需要三种能力:一是销售,这是最容易的,招点人,搞搞宣传,就可以开始卖票了,新人都很容易上手;二是行政管理和技术服务的能力,这个需要一点时间来培养,尤其是涉及剧场和作品的技术部分,一个技术团队要能为世界各地不同级别的艺术团体提供技术服务,至少需要3-5年的时间来培养和学习;三是挑选和安排剧目的能力,即内容组织和策划的能力,这个是最难的部分。它需要大量的观剧基础,审美和判断力,还需要在经济和市场等多重方面对项目进行评估和抉择。不客气的说,没有10年的市场经验,很难练出来。我们团队现在基本保持着一年200部左右的观剧量,而且大部分都是在国外的艺术节和剧场中看,光这个“阅读量”,就很难有人跟我们拼。
某种程度上,“爱丁堡前沿剧展”就像是我们的样板房,通过带着这个样板房到处走,很多人看到了我们选戏的品味和能力,也看到了我们设计和包装一个剧展或者说流动的艺术节的能力。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希望能够将这种能力与他们的需求结合起来,也因为这种需求,我们开始向一个艺术节的“策展机构”转型——在“爱丁堡前沿剧展”之外,根据不同主体的需求以及它的特殊性,为其提供内容的组织和策划工作,它可不是一种简单的拼盘式菜单,而是需要将所有内容与需求方的条件深度整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度身定做”的策展人和内容供应者。
最近的一个案例是在杭州西溪发生的“西溪国际艺术节”。2014年5月,我被带到一个空置了多年的空壳剧场里,业主方希望我们可以来接手这个剧场,但被我们婉拒了。可是那个空间非常独特,我也很喜欢它所在的西溪天堂片区,觉得杭州是需要这样一个剧场、并让众多精彩作品在其中发生。所以我接下来的主要工作是说服业主:我不做这个剧场,但我可以教你们怎么做,从担当剧场设计顾问,到为其规划财务分配方案、设计开幕演出季的内容等等。他们又惊又喜的接受了这个建议,一切很快走上轨道。
在这个原来规划只有220座小剧场的基础上,我和设计师一起,重新修改设计图和座位布局,将其改造成一个拥有400个座位的中型剧场,同时还兼有排练厅等多种开放性功能。朴素、现代、将空间利用到极致的设计,在财务上增加了足够的灵活性,节约出来的经费,则可以用于内容的采购。
原来聚焦于戏剧的“开幕演出季”,被升级为一个“国际艺术节”,这种飞跃将我们迅速带离了原有的舒适地带,迫使我们不能再依赖这十多年来形成的戏剧优势,而必须同时平衡音乐、舞蹈、戏剧等多个板块。当然,这种“自我逼迫”,也再次帮助我们团队的策展能力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成为一个在表演艺术领域拥有多元视角和选择能力的策展者。在西溪国际艺术节中,有内容合作方上海世界音乐季组织的大量户外和室内音乐节目,也有我们自己在阿德莱德艺术节挑选的原生态弗拉门哥舞蹈《塔巴罗》和古典吉他天才汤姆,沃德,都在艺术节期间有上佳表现,观众非常喜欢。这也给了我们以极大的信心,让我们可以在这个方向上走得更远。
与此同时,我们还担当了上海虹桥天地演艺中心2015开幕演出季的策展机构。在这个技术操作极其高难度的White Box中,我们请来了今年刚刚登上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主单元的剧目《龙》,由苏格兰国家剧院和天津儿童艺术剧院合作的大型视觉形体剧,这是一部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跨国合作作品。《安德鲁与多莉尼》、《反转地心引力》、《迷失》等剧目也将陆续上演,为这个建在亚洲最大交通枢纽旁的剧院,提供内容上的饕餮盛宴,服务上海和“华东2小时经济圈”内的观众。
在转型为艺术节策展机构的过程中,最大的收获是:我们终于可以借用合作者的力量,去做一些本来单靠自己的力量所不能完成的事。因为每个合作者,都有他自己的资源和优势,如果你能充分利用与发掘,就是对自己能力边界的一次巨大拓展。明年,我们还将在上海两个新而重要的艺术节和开幕演出季中担任策展工作,届时,又会有一些全新的作品,经由我们和合作者的努力而一同呈现给上海以及周边观众。
而我个人,也在这一次又一次的新合作中,学会了尊重、隐忍、积极沟通和绝不放弃。
要很多人一起努力,这世界才能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