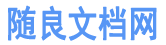《南词叙录》是我国明代著名艺术家、文学家兼戏剧家徐渭(1521—1593)的戏曲论著,是我国整个封建时代里唯一的一本有关南戏的专论。
在《南词叙录》之前,我国也曾出现过不少有关戏曲的论著,较为著名的,如元·夏伯和的《青楼集》、钟嗣成的《录鬼簿》、周德清的《中原音韵》、燕南芝庵的《唱论》及明·朱权的《太和正音谱》,等等。这些论著,或描述艺人生涯,或著录作家作品名目,或标列戏曲声腔体式,或制定音韵谱律,或传授歌唱方法,它们的主要贡献,是在于为我们保存下许多有关北杂剧方面的可贵资料,而直接涉及戏曲艺术创作见解的,并不太多。《南词叙录》不同于上述诸作的一个显著特色是,作者在提供有关南戏源流、发展、风格、特色、声律、文辞、剧目方面的珍贵资料以及对方言、术语的考释等的同时,还提出许多重要的戏剧见解,这些见解,今天看来,对于我们仍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一
徐渭写作《南词叙录》的动机之一,就是想恢复长期以来被人所歧视的南戏的历史地位,以促进它的顺利发展。他认为,北杂剧、金院本、元散曲都已有人予以详尽的记载或对作品加以辑集,“惟南戏无人选集,亦无标其名目者,予尝惜之。”(注1)在徐渭看来,南、北曲的历史地位至少应须同列;北曲固有北曲的长处,而南曲也有南曲的“高处”。他说:“有人酷信北曲,至以伎女南歌为犯禁,愚哉是子!”徐渭的这番指责,是有它明确的历史与现实的针对性。南戏是民间产物,相传在南北宋间发源于浙江温州,号称“永嘉(温州)杂剧”。它原是一种地方小戏,后来逐渐流布于南方各省的广大区域,成为具有多种声腔的剧种。由于它最初是“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不叶宫调”,所以封建“士夫”对它“罕有留意者”,有的剧本甚至遭到官方的“榜禁”(注2)。元统一中国后,元杂剧在南方剧坛上“一时靡然向风”,南戏更处于受压抑的地位。不仅元统治者对它相当冷漠,就是那时的一些文人也多持偏见,有的还把南曲看作是“亡国之音”(注3)。南戏的这一命运,到了元末,稍有转变。由于那时北剧衰微,而南戏却在同北剧的交流中汲取了新的养分,使自己的艺术形式更趋完美,再加上这时产生了象高则诚的《琵琶记》这样艺术成就卓著的作品,南戏的影响扩大了。继之,南戏“作者猖兴”。入明之后,继承民间南戏传统的传奇之作,呈现空前繁盛的景象;各种南曲声腔,日相繁衍,获得旺盛的生命力。尽管如此,南戏受歧视的地位并没有完全改变。除统治者一直把它视作不登大雅之堂之外,文艺保守势力还予以种种非难。比如,有人曾把南曲声腔的蓬勃繁衍,硬说成是“愚人蠢工,徇意更变”,而将体现南曲创腔成果的海盐、余姚、弋阳、昆山四大声腔,斥为“杜撰百端,真胡说也”(注4)。所有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封建“士夫”阶层对于民间戏曲的偏见。在此情况下,徐渭的《南词叙录》以其鲜明的倾向性,发表了不同凡响的议论,热情地肯定了来自民间的南戏的应有地位,这在当时的封建文人中,可说是独树一帜。
《南词叙录》里的见解,又是针对当时明传奇创作实际而发的。就在民间南戏受到文艺保守势力歧视、排斥的同时,,另有一批封建复古派文人却利用了南戏的形式,把它引向了“以时文为南曲”的创作邪途。他们用封建说教,叛离了南戏的人民性;在表现方法上,以空泛的“经子之谈”,代替了生动的艺术形象创造。这种创作倾向,从邱濬的《五伦全备记》和邵璨的《香囊记》等开始,在明代剧坛上足足蔓延了一个多世纪,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南戏的健康成长,到徐渭写作《南词叙录》的嘉靖年代,其危害所及,已造成如徐渭所讲的“南戏之厄,莫甚于今”的严重程度。鉴此,《南词叙录》在批判“以时文为南曲”的错误创作倾向的同时,充分肯定了南戏的固有特色。徐渭说,民间南戏虽然“皆俚俗语也”,然而却有其“高处”,这就是:“句句是本色语,无今人时文气。”这些出于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的书会才人和勾栏艺人之手的作品,具有一定的生活气息,它决非是那些脱离群众实际生活,专凭“经子之谈”的封建复古派文人所能“辏补成篇”的。徐渭也十分肯定文人重创的南戏作品《琵琶记》,但却有他自己的标准。他不同意“《琵琶记》高处在《庆寿》、《成婚》、《弹琴》、《赏月》诸大套”的见解,而认为“《食糠》、《尝药》、《筑坟》、《写真》诸作,从人心流出”,才是“最不可到”。又说:“如‘十八答’,句句是常言俗语,扭作曲子,点铁成金,信是妙乎。”《琵琶记》中《食糠》诸折,恰恰是最能透露原来流传于民间的《赵贞女蔡二郎》戏文的本来面目,由此可以看出他对于民间戏文特色的倾注。
徐渭在他自己的戏剧创作中,也很注意汲取民间养分。如他写的由四个独立短剧合成的《四声猿》(《狂鼓史》、《玉禅师》、《雌木兰》、《女状元》),以及相传也是徐渭的作品的《歌代啸》杂剧等,大抵取材于民间流传的故事。在表现方法上,也保留着民间戏剧与其它民间艺术的某些表现手法。比如,《玉禅师》第二出写月明和尚向柳翠说法时采用的哑剧形式,直接来自民间歌舞。(注5)再如,《狂鼓史》中两个歌女所唱的“一个低都呀”、“一个冬哄呀”之类的歌子,它是作者对民间俗唱形式的一种融化创造。《四声猿》的曲白,遣词用语,毫无雕饰,质朴无华,野味甚浓,这是一般不熟悉、也不注重学习民间语言的文人们所没法写得出来的。
从明初被大批粉饰太平与宣扬封建意识的“宫廷杂剧”主盟剧坛的局面,到明中叶“以时文为南曲”的戏曲逆流泛滥成灾,曾使明戏剧艺术一度脱离了现实与群众,日趋僵冷,这时,徐渭的《南词叙录》连同他的戏剧创作,就好比是一股夹带泥土芳香的清新暖气,正奋力催促着戏剧新春的降临!
二
如何看待剧本文辞与戏曲音律,曾为明中叶以后的剧坛所争论不休,尤其是在徐渭年代稍后一些的“汤(显祖)沈(璟)之争”,更是冰炭不可相容。争论的焦点,实质上就是如何看待戏剧艺术特性,亦即如何看待舞台演出效果的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南词叙录》提出了一些颇为独到的见解。
徐渭在戏剧与文学的主张上,力主保持“本色”。对待剧本文辞,他强调要“浅近”“易晓”。徐渭抨击了从明初邵璨的《香囊记》以来“以时文为南曲”的弊病。他指出,邵璨“习《诗经》,专学杜诗,遂以二书语句匀入曲中,宾白亦是文语,又好用故事(典故)作对子,最为害事。”至于以后那些效颦《香囊记》的文人传奇之作,更是“无一句非前场语,无一处无故事,无复毛发宋元之旧”,使南戏作品的创作传统遭致空前的践踏。针对这种状况,徐渭提出了“与其文而晦,曷若俗而鄙之易晓”的主张。他的理由是:“曲本取于感发人心,歌之使奴、童、妇、女皆喻,乃为得体。”这里,徐渭正是抓住了戏剧语言的特征。他要求剧本的文辞必须从它宣传的对象出发;他反对把剧本搞成只是仅供少数士大夫吟咏品赏的“案头之书”。他提倡戏剧语言要有舞台的生命力,要能为多数的观众——其中包括只能听懂自己熟悉语言的台词,而不能认字知书的“奴、童、妇、女”们——所能接受和欣赏。这正道中了戏剧语言功能的实质,说到了舞台语言效果的点子上。
但另一面,在强调戏剧语言要力求“本色”的同时,徐渭也并不排斥文人对戏剧语言进行加工与提高。他指出,“南曲固是末技,然作者未易臻其妙”,要写好它也是不容易的。在徐渭看来,戏曲歌词并不是实际生活语言的照录,而应有它自身独有的艺术风采。他所反对的只是“词丽而晦”。就是说,他认为戏曲语言既要能如实表现生活,又要能体现艺术的“美”,只有把这二者结合起来,方能更好地收到强烈感染观众的舞台效果。所以徐渭才十分肯定高则诚的《琵琶记》的成就,说它是“用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于是村坊小伎,进与古法部相参,卓乎不可及已”;尤其是对《琵琶记》中那些把“常言俗语,扭作曲子”,雅俗共赏、“点铁成金”的曲词,更是称赞备至。他还深感遗憾地认为,过去之所以“南(曲)不逮北(曲)”,也正是因为:“宋时名家未肯留心;入元又尚北,如马、贯、王、白、虞、宋诸公,皆北词手;国朝(明)虽尚南,而学者方陋:是以南不逮北。”这种既要求戏曲语言普及于观众,作到人人“皆喻”,又强调作家加工、提高,使之“臻其妙”,确是一种比较周到的见解。
在对待戏曲音律的问题上,徐渭强调要“顺口可歌”。这是从体察表演者的角度来强调舞台实效,希望更大限度地发挥演员的艺术表演能量。徐渭最反对那种用“南九宫”曲谱来限制南曲制作的搞法,把它斥责为“无知妄作”。他认为,南戏源自“永嘉杂剧”,其曲调是“村坊小曲而为之,本无宫调,亦罕节奏,徒取其畸农、市女顺口可歌而已,谚所谓‘随心令’者,即其技欤?间有一二叶音律,终不可以例其余,乌有所谓‘九宫’?”在徐渭看来,某一剧种音乐体制的形成,是该剧种历史的产物和艺术实践的积累,我们不宜超越该剧种音乐体制的规律、特点,强制把它纳入主观的模式,否则,张冠李戴,“最为无稽可笑”,结果令歌者无法“顺口可歌”,也就难以收到艺术实效。徐渭这种反对脱离艺术实践而主观强制宫调于南曲的提法,其精神当然是可取的,这里需补充说明的一点是,南戏音律自宋代发展到了元末高则诚作《琵琶记》的时候,已是相当的进步,自有一套乐曲组织规范。后来到明中叶,昆山腔崛起,腔调变了,且格律日趋严格,如拿它和以前的南曲音律相比,自然又有许多的不同。明人不懂此中的道理,往往用昆山腔之律去衡量所有南戏,觉得处处不合律,便误解为它都是没有宫调格律的。这种误解,徐渭也在所不免。
然而,徐渭是否就一概反对南曲要有格律呢?也不尽然。《南词叙录》说:“南曲固无宫调,然曲之次第,须用声相邻以为一套,其间亦自有类辈,不可乱也。”又说:“凡曲‘引子’,皆自有腔,今世失其传授,往往作一腔直唱,非也。若〔昼锦堂〕与〔好事近〕,‘引子’同,何以为清、浊、高、下?然不复可考,惜哉!”在强调音律“顺口可歌”的前提下,徐渭不仅不反对,而且还是提倡要严格遵循南曲合理的曲调连缀格式,以及讲求字音腔调的“清、浊、高、下”之分。否则,在他看来,大家都随便乱了套,胡唱一通的话,就连“艺术”也称不上,还哪来的“效果”?
徐渭自己创作的剧本,很少受格律、体制的限制。他的《四声猿》四个杂剧,不仅出数不等,而且曲调有的用北曲,有的用南曲,有的有意犯调。比如,《狂鼓史》演祢衡阴间击鼓骂曹,剧情基调激越,宜用北曲,更能表达祢衡那种烈火般的激情,以收到如前人所评论的“如怒龙挟雨,腾跃霄汉”的效果;又,这样的剧情、内容,不好轻吹慢打,纤回徐转,所以作者只用单出的篇幅,二千余的文字,紧锣密鼓,一气呵成。再如,《雌木兰》与《女状元》两剧,写的都是女性为主角的题材,主题也相近似,但《雌木兰》用北曲,《女状元》却用南曲。这是因为前者是表现花木兰戎装保国的斗争生活,适宜于用“使人神气鹰扬”的北曲来唱;后者则写黄崇嘏领袖文苑的才能,需用“流丽婉转”的南曲。这样,一个巾帽英雄,一位裙钗楷模,一武一文,配以曲调上的一北一南,方显得各尽其妙,相得益彰。这样,唱戏的,可以按照剧情与乐曲,尽情演唱;听戏的,又能适应习惯与爱好,毋感雷同。《四声猿》体制和曲调的精心安排,正是徐渭看重戏剧舞台演出效果的体现。
三
贯穿在《南词叙录》里还有一种鲜明的观点,就是在徐渭看来,任何文学艺术都是因时、因地在变化、发展的;我们对戏剧艺术也需用这种变化、发展的眼光去考察它、评价它。比如,徐渭对戏曲声腔的见解正是如此。徐渭热情肯定了南戏不断创制新腔的成绩,在《南词叙录》里,他较详细地记录了当时南戏四大声腔的流布情况,而对其中刚刚兴起不久、遭到文艺保守势力非议的昆山腔,更是称赞不已,说它“字虽不应,颇相谐和,殊为可听,亦吴俗敏妙之事”,“流丽悠远”,“听之最足荡人”。针对保守派对昆山腔的非议,徐渭提出:“或者非之,以为妄作。请问:〔点绎唇〕、〔新水令〕是何圣人著作?”在徐渭看来,象〔点绎唇〕、〔新水令〕之类的北曲曲子,早先也不过是民间乐曲而已,它们都并非出于哪一位“圣人”的创造,它们之所以后来被大家所认可,是因为它们在长期的戏曲音乐实践中经得起检验的结果。北曲发展的历史事实既是如此,那末,现在新生的南戏声腔昆山腔刚一出现,怎么可以马上对它妄作非议呢?南戏声腔发展的一个历史事实,——在徐渭之后,曾被文艺保守派所不屑一顾的昆山腔,竟发展到处于压倒其它各种戏曲声腔的地位,——证实了徐渭的见解是非常敏锐、精到的。
徐渭非但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戏剧,而且尊重不同地域的剧种特色。他对南、北曲不同风格、艺术效果的比较、估价正是如此。关于北曲,他认为它是“辽、金北鄙杀伐之音,壮伟很戾,武夫马上之歌,流入中原,遂为民间之日用”;听北曲的效果,可以“使人神气鹰扬,毛发洒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信胡人之善于鼓怒也。”关于南曲,他认为它是“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听南曲的效果是:“纤徐绵,流丽婉转,使人飘飘然丧其所守而不自觉,信南方之柔媚也。”他把南、北曲不同风格与艺术效果的形成,看作是不同地域的人们生活的必然反映结果。这种判断,无疑很有可取之处。上面已经说到,徐渭写作《南词叙录》的用意,是想抬高被人歧视的南戏地位,因此,他自然会较多肯定南戏的优点,但他却并不因此去掩饰南曲的缺陷、抹煞北曲的长处,借此来“拔高”南戏的地位。出于认为一地自有一地的戏曲特点、必须尊重各地剧种声腔特色的观点,徐渭还是比较客观地估计了南、北曲的各自长短之处。如说:“南之不如北有宫调,固也;然南有高处,四声是也。”又说:“南易制,罕妙曲;北难制,乃有佳者。”他既极力反对那种尊北贬南的历史偏见,而又强调指明由于“南曲绝少名家”而导致的“南不逮北”的客观事实。
北杂剧的繁荣时代是在元前期,到了明代,虽然也有一些人还在写,作品的数量亦洋洋大观,而且也出现少数较好的作品,但杂剧总的趋势已成强弩之末。徐渭自己也是用杂剧形式来创作剧本的,但它再也不是固有的一套杂剧格式了。由于感到北杂剧原有那套如四折一楔子、一折之中一般只能由一角唱北套曲等等的旧规,同发展了的戏曲已不相适应,于是徐渭在创作中对杂剧体制作了大胆的改革。在徐渭之前的贾仲明、朱有燉、王九思等人,虽然也曾鉴于旧有杂剧体制的拘束,在创作中对杂剧体制有所改革,开始出现如“南北合套”、不受四折一楔子的限制、写单折杂剧等等的搞法,但还远不如徐渭的大胆。徐渭是第一个只用南曲曲牌写杂剧的作家,首创了所谓“南杂剧”的形式。徐渭在戏剧创作中这种大胆突破、勇于改革的精神,是与他以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戏剧的见解不无关系的,因为到了徐渭的时代,各种南曲声腔竞相繁衍,已汇成戏曲声腔的主流,因此,在他所写的杂剧作品《女状元》里,就按照这种戏曲声腔发展的现实趋势,以及根据该剧剧情内容的需要,作出这种大胆革新的尝试。
四
前人评论徐渭,好喜欢用一个“奇”字。如:“梅客生尝寄予书曰:‘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注6)又如:“徐天池先生《四声猿》,故是天地间一种奇绝文字。《木兰》之北与《黄崇嘏》之南,尤奇中之奇。”(注7)如果他们这些人也肯留意这本《南词叙录》的话,恐怕也会惊叹为“奇著”的了(从《南词叙录》从未被收进各种徐渭文集的事实来看,说明过去人们对它是很少留意的)。确实,《南词叙录》无论从选题到见解,在当时来讲,都是别出心裁,是一般文士们所不会也不能为的。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徐渭之所以能写成这样的戏曲论著,正同他的诗文与剧作一样,是跟他先进的思想、反叛的精神、狂放的性格,以及在艺术创作上一贯勇于探索、创新的精神分不开的。徐渭是晚明进步思想家们的前驱之一,冲决旧观念,反叛旧传统的精神十分强烈。正由于这样的原因,加上他多方面的艺术才情,使他无论在诗、文、书、画各方面的创作,都能挣脱前人束缚,自成其一格。另外,他在浙江总督胡宗宪部从军期间,又多年往来于浙、闽一带南戏广泛流行的地区,使他有机会进行有关南戏艺术的实地考察。这些都是徐渭能够写出这本一反时人陈见的戏曲论著的原因所在。
最后,我们还需强调指出,《南词叙录》毕竟还是旧时代文人的著作,它虽然能提出上述那些值得我们肯定的戏剧见解,但总的看来,还是不很完整的。它侧重的还仅停留在南戏的文辞与音律等上头,而对于戏剧理论中的其它重要课题,比如戏剧的社会功能方面的问题,它似乎有意回避了。作者还无法自觉认识到,作为观念形态的戏剧艺术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这一道理。因此,他看重民间南戏的艺术创造能力,但却没有注意到民间南戏所反映的丰富的人民群众的生活内容;他强调戏剧的舞台演出效果,但却不曾联系作品的思想实质;他意识到戏剧发展与地域特色形成的必然性,却不见构成这种必然性的真正社会因素;他能看出当时“以时文为南曲”戏曲逆流的弊病,却无法全面解释这种弊病形成的真实原因。但尽管如此,徐渭在《南词叙录》里所体现的上述那些戏剧见解,对于我们研究传统戏曲艺术的发展,进一步提高戏曲艺术的创作水平,多少是有一些借鉴意义的。
(注1)凡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见《南词叙录》(据中国戏曲研究院编校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
(注2)明·祝允明《猥谈》载:“予见旧牒,其时有赵闳夫榜禁,颇述名目,如《赵贞女蔡二郎》等。”
(注3)见元·周德清《中原音韵》所记“前辈余论”。
(注4)同(注2)
(注5)清·陆次云《湖堧杂记》记载,杭州正月上元灯节有演月明和尚戏柳翠的跳舞风俗。又据明·刘侗《帝京景物略》记载,北京正月亦有“戴面具,耍大头和尚”的民间歌舞。
(注6)明·袁宏道《徐文长传》。
(注7)明·王骥德《曲律》。